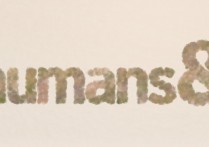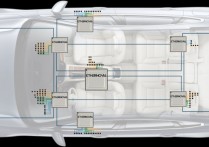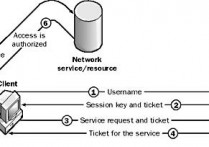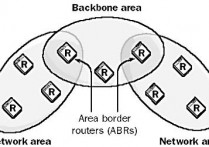我們不是懷念2016年——我們懷念的是網路,還沒出現那些爛東西
對新一代而言,2016年現在被稱為「最後一個美好的一年」。

自新年起,Instagram 被 2016 年主題的「新增你的」貼紙取代,鼓勵用戶分享 2016 年的懷舊照片。用戶已發表超過 520 萬則回應,激起足夠的話題波及其他平台。在 Spotify 上,用戶自製的「2016」播放清單自新年以來增加了 790%,該公司現在在 Instagram 簡介中自豪地宣稱「再次浪漫化 2016 年」。
公平地說,2016年看起來確實是個比較簡單的時代。唐納·川普還沒在白宮任職一天,沒有人分辨 N95 和 KN95 口罩的差別,Twitter 當時仍叫 Twitter。那是「Pokémon Go 夏季」的一年。
但如同常見的情況,懷舊情緒掩蓋了當時已經明顯的焦慮。當迷因圖書館員Amanda Brennan在她的檔案中搜尋定義2016年的圖片時,她給我看了一張截圖,讓我感到驚訝,畢竟網路上對這個年份的熱度非常高漲。貼文寫道:「真不敢相信魔鬼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2016年」,另一位用戶補充說:「就像他有個作業要在2017年1月1日交,卻直到現在才忘了。」
我忘了當時大家有多討厭2016年。那是脫歐之年,敘利亞內戰的高潮、茲卡病毒爆發,以及Pulse夜店槍擊事件,僅舉幾個令人恐懼的來源。這不僅僅是唐納·川普的兩極化當選——就在那晚之前幾個月,一位Slate專欄作家真誠地提出問題:2016年與臭名昭著的可怕年份相比,如1348年黑死病肆虐,或1943年大屠殺高峰期,究竟有多糟。

新的一年開始是懷舊的肥沃土壤。網路靠這種吸引互動的誘餌蓬勃發展,以至於 Facebook、Snapchat,甚至內建的 Apple Photos 應用程式,都不斷提醒我們一年前在做什麼。
不過這次,我們的懷舊感覺不同,而且不只是政治上的。隨著 AI 越來越深入我們在網路上的一切,2016 年同時也代表了演算法™接管前的一個時刻,當時「糞化」尚未達到無法回頭的地步。
為了更好地理解2016年網際網路的狀況,布倫南建議將它視為2006年十週年,那時社交網際網路終於在我們生活中穩固了自己的地位。
「2006年,科技發生了變化。Twitter 成立,Google 收購 YouTube,Facebook 開始允許任何 13 歲以上的人註冊,」Brennan 告訴 TechCrunch。
在社交平台之前,網路是那些尋找社群感的人的地方——正如布倫南所說,這些人「缺乏更好的詞彙,就是書」。但當社群媒體興起後,網路開始洩漏,流行文化與網路文化之間的隔閡開始瓦解。
「到了2016年,你會看到十年的時間讓人們進化,那些本來就不是網路宅的人,可能會進入4chan,而這些以前由網路使用者組成的小地方,與那些不那麼上網的人形成,」她說。「而且,因為有了手機,現在大家都算是網路使用者了。」
依照布倫南的估計,2016年是佩佩青蛙——曾經是網路漫畫中和藹的迷幻者——被腐化成仇恨象徵,而推動遊戲門事件的厭女症也出現在全國政治舞台上,這也說得通。(同時,左傾的迷因團體內部爭論著「dat boi」迷因——一隻青蛙騎獨輪車的圖像——是否挪用了非裔美國人的白話英語。)
當時,指出網路文化如何開始影響我們的政治現實,感覺很新鮮。再過十年,我們就有一個以迷因命名的偽政府機構——這只是眾多暴行之一——削減了國際援助資金,導致數十萬人死亡。
又過了十年,我們已經有整整二十年的時間去面對社群網路如何塑造了我們。但對於2016年還是孩子的人來說,這一年仍帶有某種神秘感。Google 搜尋效果很好。辨識深度偽造相對容易。老師不必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判斷學生是否從 ChatGPT 複製貼上作業。交友軟體依然充滿希望。Instagram 上的影片並不多。《漢密爾頓》很酷。
這是對一個網路時代的樂觀看法,雖然它本身也有一堆問題,但同時也呼應了更類比生活方式的潮流——正是促使實體配對活動和傻瓜數位相機復興的現象。社群媒體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如此核心,已經不再有趣,人們想回到那個沒有人說出「末日滑動」這個詞的時代。誰能怪他們呢?